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在北京电影节上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媒体关注,他说:“你说你们要保护,要分级,这是事实。但,你要明白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是的,你们因为要保护国家不受分裂势力干扰而不碰一些敏感题材,这个我理解,但,上帝啊,你不能不面对你的历史啊。我真的非常努力、非常希望在中国做合拍,但,我失败了。”斯通先生说的句句是实话,但是他应该在美国说,中国人大老远把你请来,奉为上宾,你却满嘴跑火车,你知道你回去后有多少人会跟着遭殃吗?
我猜《环球时报》几天后会发表一篇驳斥斯通“荒谬”言论的文章。
奥利弗·斯通来自一个没有广电总局的国家,他自然不清楚电影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言无禁忌,恰恰触碰了中国人的最敏感神经,或者说过去几十年官方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历史。
奥利弗·斯通不知道,在中国,涉及到出版、传播领域都有审查,尺度也跟橡皮筋一样,没有标准。他更不知道,有很多题材一直属于禁忌范围。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所以都跟高山障碍滑雪一样,一路闪躲腾挪。美国人拍电影只知道拍出来根据级别到哪个电影院里放,有第一修正案摆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拍不了的。
你看其他被请来的导演,都心知肚明,没有人愿意提这个敏感问题。中国电影市场很大,连好莱坞都在电影里拍中国人民的马屁,目的就是希望能在中国电影票房中分一杯羹。只有这个奥利弗·斯通,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应该被列入不受欢迎的黑名单,直到他忏悔,当众承认错误,否则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会被伤害的。
其实,以往两会的时候,会有委员提出来给中国电影分级,但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电影审查制度,会发现,这个审查制度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限制言论和创作表达,怎么可能取消呢。
中国电影目前不可能分级,很多人举出各种例证证明分级的好处,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最清楚了,要是对他们有利,早就分级了。咱们不说意识形态,这是个复杂问题,牵扯得太多,咱们说一件跟分级有关的简单事情,你分级怎么分?按照目前任何国家采用的电影分级制度都会触及中国现有的法律。中国法律明确规定有“制售淫秽物品罪”,如果分级,你让不让人拍毛片?如果不让,那分级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让,那不违反刑法了吗。所以,你要不要修改刑法?如果刑法修改了,那图书、电视、电子媒体……也可以制售淫秽物品了。那秦火火该多冤枉啊。
分级是制定一个为了保障各种表达自由的规则,这是分级的目的。如果做不到,也就谈不上分级了。在中国,不可触及的领域没有规律可言,你不知道哪片地方是雷区。就算电影有了分级制度,它还是要面临规则之外的粗暴干涉。至于斯通先生说的面对历史,那是俺们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要求。
奥利弗·斯通先生,来世再考虑跟中国合作拍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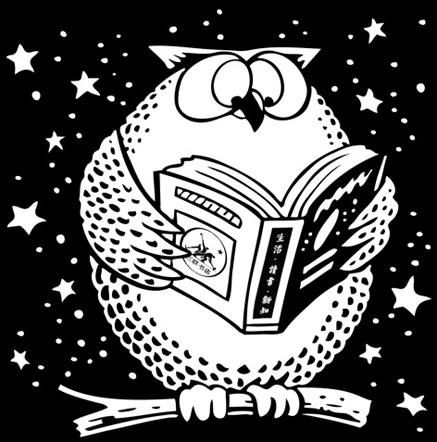
我们三联书店从4月8日开始试运营全天营业,在中国人从来没有看书习惯的任何时代,在数字化新媒体时代,在一个娱乐休闲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假如十年前三联书店这么做,一定会很热闹。
我第一次逛三联书店还是在80年代,那时候它还没有这么气派,蜗居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挑书都得撅着屁股。后来,美术馆东街22号盖好了,三联书店搬进去了,一时间门庭若市。三联书店和不远处的涵芬楼书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经常去五四大街,从朝内小街骑自行车一路向西,朝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的书店,到了美术馆,路边都是书报摊,一直伸展到现在的红楼一带。这条街基本上伴随我度过了大学四年生活,我当时有个固定习惯,周末会骑车到这里扫街,如果美术馆有影展画展,还可以进去看看。后来,政府部门可能觉得路边都是书报摊,影响市容,或者,那些书籍中经常夹杂一些反动淫秽色情的内容,干脆就给清理掉了,当时我可是在这些书报摊上淘登到不少好书,可惜的是,在大学宿舍被同学拿来拿去都有去无回,只有一本《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因为我给它包了一个书皮,上面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人民大学出版)”才幸免遇难。
所以,这些年我和很多人一样,真的是看着传统书店日渐衰落凋零下去。三四年前,我去这两家书店买书,结账时还要排队。现在,店里冷清到常常感觉自己是在做盘点的店里员工。别说三联书店了,就是王府井书店也没有几年前的热闹景象了,我每次路过王府井书店,都会有种错觉,这家书店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二三线知名品牌大卖场的。
有些趋势是我们都无法阻止的,比如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新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出现,它在千方百计蚕食着传统媒体行业,逼着你不得不转型,甚至死掉。
书店对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梦一般的回忆,当我们渴望去了解世界时,书店往往扮演着通向世界码头的角色,我们在书店里寻找自己渴望看到的那本书,每一次我们走得更远,可能都会跟一本书有关,而这本书来自书店。
如今,我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到自己想看的书,过去,不读书看报,很难获得你想要掌握的知识,但是现在你可以通过网络知道世界上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书或者书店对我们越来越不重要,慢慢走出我们的生活了。
这时三联书店决定全天营业,可以扭转传统书店的被动局面吗?难说。
先看看都是些什么人晚上不睡觉还在外面逛,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类人:上夜班者、神经衰弱者、生物钟颠倒者、白天不坐班可以自行支配时间者、心情失意者、乞丐……这些人是潜在走进“夜三联”的群体。
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是潜在的“夜三联”读者或者说购书者呢?我猜大概有这样几类人:夜猫子且过去有看书习惯的人、写作者、喜欢购买打折商品者……这类群体有多少呢?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口,看纸质书习惯的人估计能有0.5%,在市区内的人估计占这类人群的50%,如果同时又喜欢熬夜或生物钟颠倒或者有写作习惯的人或者……我猜大概凤毛麟角了吧。不过没关系,毕竟三联书店面积不大,不像娱乐场所的夜店可以摩肩接踵,能凑个百八十人倒是可能的,上半夜甚至会更多。问题是,什么动力会让他们出来?
三联书店的楼上是雕刻时光咖啡馆,这里倒是经常人满为患。据说雕刻时光会和三联书店一样变成全天营业。表面上看,二者形成的业态可以吸引人夜里出来一坐,或呼朋唤友,或三五成群,会让这两家店共同营造一种带有小资和文化品位的夜生活。可是仔细一想,人们晚上不睡觉,除了宵夜就是在夜店里闹腾,雕刻时光的环境不太符合人们的消费习惯,它太素而不太俗。雕刻时光真能引来夜客吗?我看悬。
北京三里屯有个书店叫PageOne,它坐落在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地区,却可以全天营业,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去三里屯的人都是都是夜生活消费的,没几个去看书的。但是你别忘了,这里的业态很好,“夜态”也很好,人流数量巨大,它是时尚休闲生活的聚散地,PageOne很快成为这片时尚休闲区域的一份子,时间长了,会把人过滤到这家书店驻足一憩。
三联书店位于一个看似文化氛围很浓的地方:商务印书馆、人艺剧场、美术馆、红楼……再远一点是南锣鼓巷,似乎地段还可以。但实际上,这里白天尚可,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气,甚至有些黑灯瞎火,旁边的饭馆差不多九点多钟就开始轰人,路边基本上打不到出租车,它实在无法营造一个像三里屯那样的夜生活环境。毕竟人们晚上出行和白天不一样,都希望到一个热闹扎堆的地方。
换句话讲,你全天营业,得给人一个说法,里面得有故事能吸引人,让美术馆东街变成一个文化标志,让那些平时都不知道书该从哪边翻的人不得不关掉手机和电脑跑过来享受这个,不然就会觉得自己落伍了……比全天营业更重要的是营销,不是说你增加营业时间、打折和改进一些服务内容就万事大吉,那样消费者只能感受一些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去,它又恢复原状了。
如果三联书店真的想成为美术馆东街上的一个地标,成为不夜书店,那必须要以一种引导消费的方式来包装自己,它可以和雕刻时光一起去策划制造一些话题,让今天的人们认为大晚上去书店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超凡脱俗的时尚特征,让一些普通人半夜推门进去,一抬头不是看见莫言在喝咖啡,就是看见崔永元在遛弯,或者看见马未都在和人聊青花瓷,最不济的你也会看到方舟子拿着一本书在运气,比着他和书谁长得更方……总之,你一进三联书店的门,名人俯仰皆是,不小心就能把你绊一个跟斗,而且只有在晚上才会这样……这是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化氛围。我相信这些名人们都有书店情结,他们都不希望传统书店就此走向没落,都会尽自己的影响力过来站台。我也相信,不需要多久,三联书店一定会变成京城第二个庆丰包子铺扬名四海。

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副好嗓子是件幸运的事,而把这副好嗓子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是幸运中的幸运。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些靠嗓子挣钱吃饭的人,比如,播音员、歌手……黄绮珊有一副让很多歌手羡慕的好嗓子,每当人们提起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她的嗓子在中国歌坛数一数二。但遗憾的是,她的这副好嗓子从来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有时候上帝总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就不会给你那个。上帝有时候好色,偏爱那些徒有一副脸蛋的人,黄绮珊的天赋被这些脸蛋淹没了,直到她已经变成了“黄妈”,才借助无聊的选秀比赛走红。
如果说黄妈过去被埋没,跟世俗的审美有些关系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她被埋没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乃至华语地区没有一个像样的制作人。在这些制作人看来,黄绮珊具有无可比拟的天赋,接下来就会走入误区,认为她什么都可以胜任,而不像对待条件一般的歌手,尽可能去挖掘他最长处的那一部分,反而更容易跳出来。黄妈在那些三流制作人眼里,不是和氏璧,而是一块现成的宝玉,让她唱什么都可以。而黄妈本人大概对自己也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在音乐话语世界里,男人还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么多年,她就是一个被人拿来做各种音乐实验的小白鼠,低能的音乐人们每次实验时都侥幸地认为黄绮珊可以成为一件成功的实验品,结果都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个叫赵钦的制作人是哪路神仙,之前做过什么专辑,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最清楚黄绮珊该怎么唱歌,他知道技巧和天赋最终是为诠释歌曲服务的,如果本末倒置,无异于害人,所以,赵钦没有走回过去实验黄妈的老路,而是删繁就简,回归本真。假如黄绮珊在20年前遇到赵钦这样的制作人,何苦今天上什么我是歌手呢。
这可能是我最近十年来听到的整体感最好的专辑,十首歌曲都非常精彩,没什么主打歌,没什么风格迥异,没什么所谓新音乐样式的尝试,没什么民族风也没什么西洋景,更没有声嘶力竭的高音。其实黄绮珊只要做到她该做的就足以证明自己了。
这是一张极其朴素的专辑,各种乐器使用相对均衡,完全围绕黄绮珊的唱来演绎。我把过去黄绮珊唱过的歌曲和这张专辑的歌曲做了对比,发现最明显的差异是:过去她唱歌是没有收敛的,倾其所能,而忘记去演绎歌曲本身所传达的情感,感觉像傻小子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次,黄绮珊的演唱似乎把自己包裹起来,让那种情感在包裹中慢慢酝酿发酵,然后娓娓道来,并且张弛有度。我猜黄妈到了这个月份,也悟出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延长起来知道轻重缓急,而不是一个万能的歌手。或者,制作人赵钦敏锐地观察到黄妈最原始的特质。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的音乐人在创作歌曲录制唱片时能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供他们模仿参照的音乐,他们都能找到自己。有时候创作就像做人一样,总是缺少那么点自信,老是看人眼色,最后迷失在一种虚假的参照系中。
《别梦》是一张乍一听毫无所谓风格特点的专辑,和现在的垃圾流行音乐营造出的矫情和虚假格格不入,但是它可以让你从中慢慢体会出黄妈从歌声中释放出的力量:伤感,苦涩以及释然。